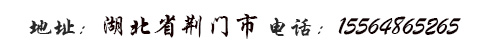和竞西中教师美文最忆母亲接年饭
|
岁月如风,新年又近在眼前。每及此时,我总会忆想起儿时母亲做的接年饭。 那时,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,物质生活十分艰窘。母亲是个要强的人,无论如何,逢年过节,都会将生活打点得有滋有味。 每年的腊月三十日(抑或腊月二十九日),是阴历年中的最后一天。在乡村,这天早晨,家家户户几乎都要将饭菜做得丰盛一些,这就是所谓的“接年饭”。 在我的记忆中,为了将接年饭做得更加精致些,此前几天,母亲就开始筹备接年饭的料物,譬如大米或小米、优质白菜、香菜、大枣、大豆、蚕豆、瘦肉、豆腐等,母亲将米或菜淘洗或择得干干净净后,心绪才安静下来。 据当地传统习俗,接年饭要早吃,也好让心中的“年”早日到来。儿时,我很好奇,也懵懂得很,经常提一些怪异的问题。有一次,我问母亲:“‘年’是啥样的?年像人一样会说话、会走路吗?”母亲前仰后合地笑个不停,回我话说:“孩子,‘年’究竟是啥样,我也说不出,反正过年是一种很吉祥、很高兴的事儿!”我没有再追问下去,心中却充满着无限的欢愉。 在盼望中,接年这天终于到来了。当我还赖在被窝里享受难得的温暖时光之时,母亲早已起身去了厨房。从门缝中看到,母亲走过来,踮过去,始终忙碌个不停。不一会儿,又听到锅碗瓢盆的响动声,是那么和谐悦耳,犹如一支优美圆润的交响乐。 母亲将洁净的米放置到锅里,从水翁中舀出两瓢凉水,清脆地倒入锅中,用铁铲子在锅里抄过来,抄过去,以确保将米浸泡过来。然后,盖好锅盖,上面再压一个铁砧子,锅盖周围还要围一圈沾湿了的长布条,以防止热气散发。这样做出来的米饭才香甜可口,有劲道,母亲后来如是说。 厨房里,母亲不停地往锅灶里添柴,风箱的“咕哒”声大约持续了半个小时后,米饭蒸熟了。母亲打开锅盖后,厨房里、内室中,顿时充盈着米饭缭绕的馨香。一种食欲催促我一骨碌爬起身,赶紧穿衣,洗罢脸,端坐到饭桌前,准备美餐接年饭。但母亲说,不要着急,接完年后方可入餐。 因为父亲早已因公患病,不能操持家务,所以儿时接年,我一直是母亲的小助手。母亲将米饭盛放在白瓷碗中,中央围成一个小“山”状,米饭上面还要点缀几个红色大枣,再添加一些菜肴,碗的边沿放一双筷子,最后,母亲将碗用方盘或圆盘托起来,和我一起去了街门外,开始举行接年仪式。 接年的程序并不复杂。母亲从方盘或圆盘中取下香烛和纸钱后,“哧啦”一声划燃了火柴,将香烛和纸钱放在地上,一并燃烧起来。这期间,母亲很庄重地端起盘子左右转圈,上下挥动几次,似乎是在祈祷或盼望着什么,虽然我猜不透母亲的心思,但可以肯定地说,那一定是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向往。正当我思绪飞扬之时,母亲叮嘱我:“赶紧放鞭炮,接年!”我则用竹竿挑起“大地红”,用香烛点燃鞭芯,“噼里啪啦”、“噼里啪啦”,粉红色的碎纸屑铺满了街门前,像是一朵绽开笑靥的花,年就这样来了! 关闭街门,退回厨房,便是我们享用接年饭的神圣时刻。母亲大碗小碗地给我们分着米饭,并将一大盆菜肴放置在饭桌的中央。我们默默地享用着,心里都充满着一种幸福与激动。香喷喷的米饭,伴着色香味俱佳的菜肴,委实是一顿不可多得的饕餮大餐。 如果说,接年饭是“年”的序幕,那么除夕夜便是“年”的壮剧。半个多世纪过去了,父母亲因年老体衰多病已相继告别了人世,但那种念念不忘的家的味道从来不会谢幕,儿时的接年饭将永远定格于我美丽的记忆中。 作者近影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#个上一篇下一篇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shuiwenghuaa.com/swhcf/9846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关于水仙的二三事amp种
- 下一篇文章: 团购丨球根种植季,复花性超好的洋水仙和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