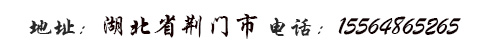观点毛海明张帆元仲一即张易考兼论元初名
|
內容提要:本文的研究對象張易,是元朝前期政治舞臺上的一個重要人物。他曾是元世祖忽必烈身邊的“潛邸舊侶”,深受忽必烈的信任和重用,官至中書平章政事、樞密副使,但却由於捲入至元十九年阿合馬遇刺事件,而被誅殺。張易在《元史》中無傳,也無碑銘等傳記資料傳世,生平事迹一直模糊不清。本文鉤稽史料,考證了元朝前期文人王惲《秋澗集》中的元仲一實際上就是張易。同時本文還討論了張易進入忽必烈幕府的時間和經過,及其在潛邸時期的若干事迹。 關鍵詞:張易、元仲一、張啓元、忽必烈、元朝 在元世祖忽必烈奪取汗位、推行漢法、建立元朝、統一全國的過程中,他身邊的漢族士人集團發揮過巨大作用,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。這些漢族士人,大多早在忽必烈即位前已被搜羅到王府或封地擔任各類工作,屬於學者所稱忽必烈的“潛邸舊侶”。及至忽必烈即位,其“潛邸舊侶”布列臺閣,成為“國朝名臣”,死後也得以追官贈爵、樹碑立傳,名耀正史。不過仍有個別例外的情況,本文的討論對象張易(?—)即屬其列。在這批“潛邸舊侶”中,張易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,早在中統元年()即首拜中書參知政事,參與元初一系列重大政策、制度的規劃擬定。到至元(—)中期,“潛邸舊侶”中很多人已經去世,存者或休致在家,或退居閑曹,惟有張易仍然長期擔任中書省、樞密院要職,“十年黃閣富經綸,落落蒼髯社稷身”,幾乎成為“潛邸舊侶”在高層政壇碩果僅存的代表。然而,這樣一位重要人物,却因捲入至元十九年()三月的阿合馬遇刺事件被處死,致使身後寂寞,聲名不彰,沒有留下碑銘行狀之類生平資料,《元史》亦因無所依據而不為立傳,世事炎涼,令人感慨。長期以來,學術界對這位神秘人物並非全無關注,唐長孺、袁冀、白鋼、王頲四位先生均著專文加以研究。遺憾的是,儘管關於張易的史料非常缺乏,但仍然有重要資料未曾引起上述學者注意,以致對張易的研究尚存待發之覆。本文首先要探討的,是元人王惲《秋澗集》中數次提及的一位13世紀中葉重要人物“元仲一”。他實際上就是張易,但却由於名字的差異而被學者失之眉睫。在論證元仲一即張易的基礎上,再對張易作為“潛邸舊侶”的幕府事迹進行若干梳理。不當之處,敬請方家指教。 一、元仲一與張易的身份特徵高度重合 關於13世紀中葉的這位“元仲一”,明確提到他的資料一共有四條,均見於《秋澗集》。其中包括一封書信和三首七律。書信題為《上元仲一書記書》,內容稍長,茲先迻錄於下: 正月十四日,王惲頓首再拜白:蓋聞居天下有二道焉,出與處而已。伏惟書記上人聰明特達,居天下至靜之中,窮聖學大衍之道,積有年矣。回視斯世,若不足玩,至於或出或處,安往而不可哉?第所可惜者時也。 朝廷嚮明而治,聖王順應而行,圖回天功,混一區宇,網羅英俊,片善俾舉。彼聞風興起者,雖山澤之芻蕘,布衣之賤士,思砥節礪行,竭力悉智,願仰副上之好賢樂善之實焉。若曰薦舉不私,用養得所,其職在於賓師之賢,遇知主上之人,朝夕引翼,一歸於正,俾賢者進而不肖者退,此天下重事,而治亂之所係也。故《傳》曰:“得士者昌,失士者亡。”又《詩》云:“濟濟多士,文王以寧。”蓋言世顯之士能如是也。 嗚呼!何君不聖,何王不明,必得聰明至靜之士見微知著,臨事不惑,斷於中而察於外,夫然後可得非常之士,而能建莫大之功。當今之時,可以與權者,舍上人一二輩,其孰與哉?若僕也,蟫蠧書史,兀坐窮年,佔畢之外,百事不解,爾來二十有八年矣。《傳》曰:“四十、五十而無聞焉,斯亦不足畏也已。”僕每讀至此,未嘗不掩卷嘆息,內增愧赧。噫!自治不勇,而喋喋於左右者,何哉?蓋僕恨以荒疏無似,不能卓然自表於世,而上人遭際乃爾,君臣之義既不可廢,今日之出,可謂千載一時也。伏惟書記上人藉有為之資,乘可致之勢,出則為王者之師,處則不失高尚其事,若僕所謂可惜者,如是而已矣,但未知生民幸不幸耳? 西狩尚遙,想當遠去,略布鄙懷,惟上人其圖之。惲載拜。 三首七律,第一首題為《贈元仲一書記》: 名寓緇衣行碩儒,蒲輪却走事巗居。萬緣擺去聊乘化,一念深來為讀書。黃閣經綸宜自重,青山談笑未全疏。相望未入廬山社,日暮碧雲思有餘。 後兩首題為《和元仲一詩韻二首》: 世事紛挐八九違,未容丘壑淡忘機。須知霖雨思賢佐,終擬卿雲挾日飛。麟閣勳名驚壯節,虎溪公案覺前非。會看杖策軍門去,滿眼行山空夕暉。 娛志詩書不厭貧,蟄龍冬臥不求伸。應憐擁篲侯門下,何似行歌澗水濱。沙鳥忘機還自樂,池蛙睅目欲誰嗔。悠悠物理吾難料,會得摳衣問上人。 四條資料當中,《上元仲一書記書》的寫作時間可以考定。書信開端即標明寫於“正月十四日”,至於具體年代,也很容易推知。因為作者王惲在信中說“若僕也……爾來二十有八年矣”,說明他這一年二十八歲。我們知道王惲生於年,那麼他二十八歲的時候就是年。也就是說,該信的寫作時間是年正月十四日。三首律詩的內容與書信互相印證,可知其寫作時間相去不遠。通過這四條資料,可以看出元仲一的一些身份特徵: 首先,他是一位僧侶。因為王惲一再稱其為“上人”,這通常是對僧侶的尊稱。加上《贈元仲一書記》首句云“名寓緇衣行碩儒”,“緇衣”是僧侶的服裝,既然“名寓緇衣”,又與“行碩儒”對舉,肯定是佛門中人無疑了。 其次,他雖然“名寓緇衣”,其行却屬“碩儒”,並未忘情世事,而是“青山談笑未全踈”,“未容丘壑淡忘機”。在《上元仲一書記書》寫作的年初,這位元仲一已經拘於“君臣之義”,即將出山“為王者之師”了。《和元仲一詩韻二首》有句“虎溪公案覺前非”,係借用東晉高僧慧遠的典故,描寫元仲一由“處”到“出”的轉變。元仲一出山后要效勞於哪一位“王者”呢?當然就是《上元仲一書記書》所言“順應而行,圖回天功,混一區宇,網羅英俊,片善俾舉”的“聖王”。只要對13世紀中葉北中國的政治形勢有所瞭解,就會知道這毫無疑問是指奉憲宗蒙哥汗之命主管“漠南漢地軍國庶事”的忽必烈。至於元仲一的“書記”頭銜,固然有可能是指寺院之職,但從王惲詩文中“黃閣經綸”、“麟閣勳名”、“杖策軍門”、“可以與權”、“藉有為之資”、“乘可致之勢”等語句判斷,“書記”應當是元仲一出山應聘的職務。考慮到忽必烈王府中設有書記一職,有理由相信,元仲一擔任的就是忽必烈王府中的書記。 從內容上看,《上元仲一書記書》顯然是一封干禄謁進的求薦信,三首七律基本上也是干謁之作。王惲對於干謁對象元仲一大力吹捧,不乏阿諛奉承之辭,足見後者是個重要人物,必非藉藉無名之輩。至於他究竟是誰,學者迄今未有解釋。按以僧侶身份出任王府書記,在當時首先可以想到一人,就是大名鼎鼎的劉秉忠。然而,劉秉忠早在年即已進入忽必烈潛邸,因此他絕對不可能是年初還面臨“或出或處”抉擇,被人慫恿“今日之出,可謂千載一時也”的元仲一。那麼,難道在忽必烈王府中還有另外一位僧侶書記嗎?答案是肯定的,他就是張易。 張易早年生活坎坷,有行乞和被收養的經歷,一度落發為僧。後來進入忽必烈潛邸,出任王府書記。相關記載,見於劉致為姚燧編寫的《年譜》: 《先君日記》云:“中統二年,奉旨令右丞相公于平陽、太原行中書省。”平陽、太原,河東、山西也,是中統、至元皆嘗行省其地。右丞,則前書記張公也。本姓魯,父名聚。社日生,小字社住,太原臨州臨泉縣使君莊人。父為人所殺,其母負公行丐於市。至郝太守家,有張孔目者無子,攜去,養以為子,因冒張姓。長祝發為僧。及遇知世祖皇帝,得所攀附云。 按據《元史》本紀:中統二年六月“以……張啓元為中書右丞”。十月“庚子,以右丞張啓元行中書省於平陽、太原等路”。張啓元即張易(對此下文再敘),故可知上引《年譜》中的“右丞相公”、“前書記張公”,就是張易。這段資料提到張易的籍貫是臨州臨泉(今山西臨縣),與其他材料互有歧異,尚有待進一步研究。而它對張易早年經歷的記載,在現存史料中則是僅見的,價值彌足珍貴。 更重要的是,按照古代文人的寫作習慣,對詩文唱酬、投贈對象一般不會直呼其名,而是稱其字號。也就是說,元仲一的“仲一”應當是字號。而張易恰好字仲一,對此有多條材料記載。當時文獻,亦時以“張仲一”稱之。如年郝經向忽必烈上《班師議》,其中有云“昨奉命與張仲一觀新月城”。王惲《中堂事記下》敘忽必烈即位前派張易聘問名士李俊民一事,謂:“己未()間,聖上在潛,令張仲一就問禎祥。”元仲一與張易,同是僧人,同為書記,還同時具有“仲一”的字號,這樣的身份特徵實在是過於巧合了。這不能不使我們強烈懷疑,他們就是同一個人。 二、元仲一之“元”取自張易法名 事實上,上文所引《姚燧年譜》關於張易的記載,唐長孺、白鋼、王頲均已加以引用並闡釋。也就是說,張易曾經出家為僧、後任王府書記的經歷,這三位學者都是知道的。既然如此,他們為什麼沒有把張易與被稱為“書記上人”的元仲一聯繫起來?為什麼沒有利用關於元仲一的史料來研究張易?原因就在於元仲一的“元”字無法解釋。儘管同是僧人,同為書記,同以“仲一”為字號,但畢竟一個是元仲一,一個是張仲一,關鍵的首字之差成為障礙。根據《姚燧年譜》,我們知道張易原本姓魯,可是難道他還姓過元嗎? 幸好有一條線索可以解開元仲一之謎,這就是張易的另外一個名字——張啓元。《元史》卷四《世祖紀一》四次提到張啓元之名: (中統元年)夏四月戊戌朔,以……粘合南合、張啓元為西京等處宣撫使。 七月……癸酉,以燕京路宣慰使禡禡行中書省事,燕京路宣慰使趙璧平章政事,張啓元參知政事。 (中統二年六月)庚申,……以不花為中書右丞相,耶律鑄為中書左丞相,張啓元為中書右丞。 十月……庚子,以右丞張啓元行中書省於平陽、太原等路。 另外,《元史》卷一一二《宰相年表》所列中統元年參知政事亦為張啓元。根據王惲《中堂事記》,可知中統元年七月到二年五月的參知政事是張易。現存史料當中,未曾發現其他人在這段時間擔任過參知政事一職。因此,基本可以肯定張易、張啓元是同一個人,相關研究也都普遍持此看法。問題就是張易為什麼又叫張啓元?對此一共有三種解釋: 一,“啓元”是張易的字。屠寄較早主張此說,但這與張易字仲一不合。王頲提出一個修正的看法,認為“啓元”是張易的“初字”,即張易先以“啓元”為字,後來才改字“仲一”。改字的原因,則是至元八年()創立“大元”國號後為避“國諱”而改。這一看法顯然不能成立。早在憲宗六年(),許衡寫給張易的信即稱其為“仲一”。而且如上文所述,年郝經《班師議》也提到“張仲一”。這說明“仲一”之字絶不是晚到至元八年以後才改的。既然在中統元年()以前,張易已經取字“仲一”了,中統元年方才出現在文獻裏的“啓元”怎麼可能是張易的“初字”呢?況且並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,元朝規定要將本朝國號視為“國諱”加以避忌,其他朝代也未見這樣的做法。 二,“啓元”是張易的號。這是白鋼的觀點。此說不無成立的可能,但也存在明顯的疑點,即提到張啓元之名的《元史》本紀和宰相年表取材于《實錄》、《經世大典》這樣的元朝官修著作,而官修著作通常不會用別號來稱呼一個人。例如許衡號魯齋,王磐號鹿庵,魯齋、鹿庵之稱只能是在私人通信、筆記、題跋或詩文唱酬投贈時使用,很難想像官修著作會將二人的名字記載為“許魯齋”、“王鹿庵”。假如張易號啓元,則“啓元”之號在私人著述當中未曾見到,反而出現在官修著作裏,這是讓人難以理解的。而且,與魯齋、鹿庵之類相比,“啓元”從字面看上去也不大像是士人的別號。 三,“啓元”是張易的別名。唐長孺持此意見。不過他在文章中只是簡單地說“張易一名啓元”,並未加以論證。此說或許較近事實,但不夠準確。從現有史料來看,張啓元之名只出現在中統年間,最晚約在中統三年,此後即不見記載。在《元史》紀、表當中,張啓元與張易二名始終不曾同時出現,而有前後之分。因此,與其說“啓元”是張易的別名,不如說是他的“曾用名”更加妥帖。那麼,這個曾用名因何而來?在我們了解張易早年的僧人經歷後,可以提出一種比較合理的解釋。 僧人出家後的稱謂與常人不同,要新取法名,不再沿用俗家姓名。具有一定地位的僧人,在法名以外往往還另有字、號。時人與之交往,也不會再稱呼他的俗家姓名,而是用法名或字、號相稱。即以張易的好友劉秉忠為例。劉秉忠前半生的經歷與張易極為相似,年輕時也曾出家為僧,後入忽必烈潛邸幕府,擔任書記。他初名侃,字仲晦,出家後法名子聰,仍字仲晦,號藏春散人。至元元年,始還俗拜官,更名秉忠。出家期間,友人詩文唱酬,通常以其字、號相稱,平時亦或尊稱其為“聰書記”。值得注意的是,其幕府同僚姚樞寫過一組五言古詩,題名《聰仲晦古意廿一首愛而和之仍次其韻》,末有自跋,云“甲寅春二月廿有七日書于吐蕃滿底城東北二百里荒山行帳中”。甲寅為年,時姚樞隨從忽必烈遠征大理。其唱和對象聰仲晦,顯然就是同在軍營當中的子聰。“聰仲晦”的稱謂,是截取法名子聰的後一字,放在其字仲晦之前,形成“法名末字+字”的三字組合。對子聰的這一稱謂並非特例。金元之際的著名“詩僧”性英,字粹中,號木庵,與士大夫多有交往。北方文壇領袖元好問在文集中一再提到性英,稱之為英上人、英禪師、粹中或木庵。除以上尊稱之外,時人還以“英粹中”一名來稱呼他。例如趙秉文有詩《同英粹中賦梅》,耶律楚材有詩《和少林和尚英粹中山堂詩韻》,段成己有詩《和答木庵英粹中》。英為法名性英之末字,粹中則係其字。英粹中之稱,同樣是“法名末字+字”的三字組合。 其實,用“法名末字+字”的“某+某某”三字組合方式來稱謂僧人,在宋元時期是相當普遍的現象。錢大昕《潛研堂金石文跋尾》卷八《楊岐山禪師廣公碑》指出: 廣公者,乘廣也。古人稱僧曰“某公”,皆以名下一字,故支道林曰林公,佛圖澄曰澄公,竺道生曰生公,慧遠曰遠公,寶志曰志公,齊己曰己公。宋、元人稱僧,或名、字兼舉,若洪覺範、妙高峰、柏子庭、噩夢堂、訢笑隱、泐季潭之類,亦取名下一字。今世知之者鮮矣。 錢大昕所說宋元時期稱呼僧人“取名下一字”,其實就是法名末字;“或名、字兼舉”,也就是“法名末字+字”的三字稱謂方式。他舉出的六個例子全都如此。洪覺範,即德洪(字覺範,—);妙高峰,即原妙(字高峰,—);柏子庭,即祖柏(字子庭,—?);噩夢堂,即曇噩(字夢堂,—);訢笑隱,即大訢(字笑隱,—);泐季潭,即宗泐(字季潭,—)。實際上,類似的例子還可以舉出很多。上面提到的“聰仲晦”、“英粹中”,顯然均屬相同情況。 張易既曾出家為僧,則必有法名。可惜文獻當中並無明確記載。在進行了上面的討論之後,顯然可以作出一個合理的推測:他的法名就是“啓元”!這樣的話,圍繞張易早年名字的所有疑問,包括“元仲一”與“張仲一”的差異,都會渙然冰釋。由於其法名為啓元,時人用“法名末字+字”的方式來稱呼他,就成了“元仲一”。像劉秉忠被稱為“聰書記”一樣,他有時也被稱為“元書記”。張易還俗之初,並未另起新名,而是僅以俗姓冠於法名之上,就成了“張啓元”。後來他重新起名張易,“啓元”一名廢置不用,所以“張易”和“張啓元”從未同時出現,“元仲一”的僧侶尊稱,更是逐漸被時人遺忘了。僧啓元(元仲一)——張啓元(張仲一)——張易(張仲一),這就是張易名字的變化軌迹。 三、張易入幕的時間和經過 在論證了元仲一即張易之後,我們可以對張易的早年事迹,主要是13世紀50年代的事迹重新進行梳理。 由於張易沒有留下成文的傳記資料,因此有關其早期生平的許多重要問題,諸如何年出生、何年出家、隸名何寺、師從何僧,全都不知其詳。比較而言,張易何時加入忽必烈潛邸幕府,似乎是一個更加重要的問題,因為這是他政治生涯的起點。學者對此有過討論,但看法不一。唐長孺推測當在“憲宗三年癸丑()或稍前”。袁冀的判斷是“憲宗四年前”。白鋼則認為“當為‘歲丁未’,即年”。實際上,王惲《上元仲一書記書》已經給我們提供了明確的答案,那就是憲宗四年(甲寅,)。如上文所言,這封書信寫於年正月十四日。寫作地點,則應當在王惲的家鄉衛州(今河南汲縣)。信中吹捧張易“至於或出或處,安往而不可哉”,“出則為王者之師,處則不失高尚其事”,同時又以“可惜者時也”加以慫恿,謂其“遭際乃爾,君臣之義既不可廢,今日之出,可謂千載一時也”。這些語句表明,在年正月,張易已接到忽必烈的徵聘,但尚未正式赴聘。另外,信中徑用“書記”職銜稱呼張易,最後又說“西狩尚遙,想當遠去”,意味着張易其實已經接受了徵聘,赴聘只是時間問題。前引王惲《和元仲一詩韻二首》之一尾聯云“會看杖策軍門去,滿眼行山空夕暉”,寓意大致相同。所謂“西狩”、“軍門”,指的正是遠征大理的忽必烈。忽必烈之前奉命遠征大理,年初班師北返。此時與王惲在衛州會面的張易,大約隨即就西行“遠去”投奔忽必烈軍營了。對此可引劉秉忠之詩為證。《藏春詩集》卷二《途中寄平章張仲一》: 觸熱從軍數載還,高家書記到何官。道存賢聖行藏裏,人在乾坤動靜間。為善不圖垂報施,濟時寧畏涉艱難。惟君胸次明如鏡,照我區區兩鬢斑。 詩中首句云“觸熱從軍數載還”,顯然是指劉秉忠隨侍忽必烈南征大理之行。忽必烈征大理,自年秋出發,至班師北還約有兩年。劉秉忠自入幕府,從軍出征,除此次外,尚有年攻鄂之役。但攻鄂之役前後只有一年,難謂“數載”,況且當時張易與秉忠同在軍中,不應有途中寄詩之事。因此,這首詩的寫作背景,應當是劉秉忠在隨軍自大理北返途中,得知張易已經西行前來軍營,因而寄贈後者。詩題《途中寄平章張仲一》,不確。此時張易尚未還俗,當不會使用俗姓,其“平章”官銜,更是至元七年()開始才有的。該題應係商挺等人在劉秉忠死後編纂《藏春詩集》時添改。 《藏春詩集》卷三《六盤會仲一飲》: 青雲自笑誤歸期,回首關山滿別離。禮樂詩書君負苦,東西南北我成癡。碧梧一葉秋風起,銀竹千林春雨垂。塞下相逢一杯酒,貴傾肝膽略無疑。 按年五、六月間,忽必烈在班師途中曾經留駐六盤山,該詩肯定寫於此時。因為首聯云“青雲自笑誤歸期,回首關山滿別離”,與班師背景相符,而且根據劉秉忠生平經歷來看,他路過六盤山大概也只在南征大理前後才有可能。毫無疑問,這時張易剛剛到達軍營,與劉秉忠“塞下相逢”,從此進入了忽必烈潛邸幕府。蕭啓慶先生指出:“年前後,可說忽必烈一生事業的奠基期。”對於張易來說,這段時間同樣是他一生事業的奠基期。 援引張易入幕的關鍵人物,學者們普遍認為就是劉秉忠。儘管史無明文,但這一推斷從邏輯上講幾乎無可懷疑。從零散資料來看,劉秉忠與張易二人經歷相符,學養相似,交誼深厚,前者又素以替忽必烈羅致人才為己任,推薦張易入幕是理所當然的事。實際上,在對忽必烈“潛邸舊侶”進行研究時,張易歷來都被歸入以劉秉忠為核心的“邢臺集團”。“邢臺集團”諸人進入忽必烈幕府,幾乎無不出自劉秉忠推薦,張易應當也不會例外。各人入幕時間可考者,李德輝、張文謙在年,馬亨在年,張耕、劉肅在年,王恂在年。相比之下,張易的入幕時間相當晚,很可能是與比他小一輩的王恂同時受到徵召。其所以如此,大概只有一種解釋,那就是張易結識劉秉忠也比較晚。如前文所述,張易的籍貫有不同說法,但無論臨泉、交城還是忻州,都與劉秉忠等人的家鄉邢臺相距甚遠,他年輕時結識劉秉忠的可能性似乎不大。目前只有一條資料表明張易在入幕之前即已結識劉秉忠,即齊履謙《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狀》: 公諱守敬,字若思,順德邢臺人。生有異操,不為嬉戲事。祖榮,號鴛水翁,通五經,精於算數、水利。時太保劉文貞公(引者按:即劉秉忠)、左丞張忠宣公(按即張文謙)、樞密張公易、贊善王公恂同學于州西紫金山,而文貞公復與鴛水翁為同志友,以故俾公就學于文貞所。 這條資料顯示劉秉忠、張文謙、張易、王恂四人曾經在紫金山“同學”,隨後郭守敬也加入了他們的學習隊伍。然其“同學”究竟係何時,却未明言。根據張文謙的神道碑,他與劉秉忠在“小學”就是同學。白鋼由此認為,張易與以上二人在紫金山“同學”的時間也是“小學”時期,具體大約在至年。然而,王恂是年才出生的,郭守敬也生於年。白鋼的觀點,實際上就是不承認王、郭二人也曾一起在紫金山“同學”的可能,也就是在没有直接證據的情況下否定了齊履謙《行狀》這段記載的真實性,未免失之武斷。按張易生年雖不詳,但估計當與劉秉忠(年生)、張文謙(年生)相去不遠,比王、郭二人都要大十幾歲。因此,如果五人確曾“同學”的話,時間不可能很早,總應當在王、郭二人基本成年之後。近年葛仁考發表論文,揭示出劉秉忠一段不為人知的經歷,即曾在年返回家鄉邢臺。葛氏因而推斷,五人紫金山“同學”之事,就發生在年之後,是以劉秉忠為核心的術數講習活動。大約在或年,劉秉忠、張文謙離開邢臺,隨從忽必烈南征大理,講習活動結束。這一推斷,雖然也還缺乏十分堅實的論據,但可以將現有的片斷材料大體理順,似乎是能夠成立的。這樣的話,張易入幕的具體背景也就容易解釋了。《藏春詩集》卷一所收一首劉秉忠與張易道別的詩作,很有可能即作于此時: 四旬未老頭先白,可笑區區紙上名。張翰且休歸故里,謝安應不負蒼生。窮通此際難開口,離合中年易動情。恨殺溪流與山色,天南地北送人行。 首句自謂“四旬”,表明此詩應當作於劉秉忠四十歲亦即年前後。考察劉秉忠的行實,自離邢回到幕府,他一直陪侍在忽必烈左右,年負責營建開平,年隨伴攻宋,其間似乎未曾離開幕府他往。同時,張易自年進入忽必烈潛邸後就與劉秉忠聚在一起,年前後也未見有離開幕府的行迹。故詩中“四旬”當是約指,該詩很可能就作于紫金山“同學”這一段經歷結束,啟程前往和林之際。此時張易或許有返回山西的打算,故而劉秉忠在詩中用西晉張翰的典故,勸他不要返鄉。同時又運用東晉謝安隱居東山不肯出仕,時人云“安石不肯出,將如蒼生何”的故事,既讚頌張易的德行和才華,也隱含勸說他出山入仕的寓意。或許正因如此,重返潛邸的劉秉忠很快就向忽必烈推薦張易,聘請他做王府書記。 元人劉敏中在為邢臺人董禧所寫的神道碑中記載:“邢為順德王答剌罕世封分邑,而太保劉文貞公、左丞張公仲謙(引者按:即張文謙。仲謙為張文謙字)實其鄉閭。若安撫李公子敬、平章張公仲一、翰林承旨王狀元先生,嘗所往來寓留。皆與公(按即董禧)交甚款,屢薦用不起。至元初,授順德諸軍奧魯千戶,非其志也。”這段話提到張易曾經“往來寓留”於邢臺,但未說明具體時間,只知道不晚於“至元初”。既然在邢臺已有結交很深的朋友,則其“往來寓留”當非匆匆路過,而是有一段滯留的時間。結合已知的張易事迹來分析,他在入幕以後,直到中統年間,恐怕都不再會有大段時間到邢臺“往來寓留”。其與董禧的交往應當發生在入幕前,極有可能就是上面所說年後與劉秉忠等人在紫金山“同學”這一階段。 綜合以上論述,可以對張易入幕經過進行如下推測。最晚在年前後,僧人身份的張易(啓元、元仲一)已經離開山西,在邢臺一帶活動。適逢劉秉忠返回邢臺,二人結識(或之前已結識,然自此始有深入交往),並與張文謙、王恂、郭守敬共同講習術數。忽必烈南征大理前夕,劉秉忠回到軍營,推薦了張易和王恂。年,忽必烈正式聘請張易擔任王府書記,年輕的王恂則被委以太子伴讀之職。年初,張易由衛州西行,奔赴班師途中的忽必烈軍營。他此時出現在衛州,有可能之前已自邢臺移居於此,也可能是從邢臺出發,先南下再折而西行,途中經過衛州。從衛州出發前,當地士人王惲致書求見,兩人見面並互贈詩作。西行路經京兆(今西安)時,還曾與許衡相逢(詳下)。這一年五、六月間,張易到達六盤山,與忽必烈、劉秉忠一干人會合,他的政治生涯就此開始。上述推測或許並不完全確切,但對於現有史料而言,大概可以算作一個比較合理的詮釋。 四、幕府時期的張易 從年入幕,到年忽必烈登上汗位,張易經歷了六年潛邸幕府生涯。關於他在這段時間的活動,史料仍然寥寥可數,很難深入討論。不過通過有限的史料,還是可以得出一個印象,那就是儘管張易入幕較晚,但在幕府中地位十分重要。 王惲《上元仲一書記書》首先給我們這樣的印象。儘管張易尚未進入幕府,但王惲對他的前景已經非常看好,稱“當今之時,可以與權者,舍上人一二輩,其孰與哉”,謂其“藉有為之資,乘可致之勢”,即將“為王者之師”,以“賓師之賢”,“遇知主上之人,朝夕引翼,一歸於正,俾賢者進而不肖者退”。甚至還預言張易的出山事關“治亂之所係”和“生民”幸與不幸。在贈詩中,也以“黃閣經綸宜自重”、“麟閣勳名驚壯節”一再勉勵。作為干祿謁進之作,上面這些話自然有不少阿諛奉承的成分,但也不能完全視為盲目吹捧。值得注意的是,當時對張易抱有較高期待的人大約並非個別,至少將干祿謁進希望寄託在他身上的不止王惲一人,以致出現了彼此競爭和排擠的現象。王惲詩中“沙鳥忘機還自樂,池蛙睅目欲誰嗔”一聯似乎就透露了上述信息,因此他又不無牢騷地說“應憐擁篲侯門下,何似行歌澗水濱”。 年,正在京兆授徒為生的名儒許衡受到宣撫使廉希憲推薦,被忽必烈下令旨任命為京兆提學,“仍給月俸”。許衡“力辭不受,往返凡六七”。在辭職過程中,許衡給劉秉忠和張易寫了兩封書信。這兩封書信並非各自寫給一人,而是寫給劉、張二人共同收閱的,因此題為《與仲晦仲一》。內容如下: 某頓首再拜兩君子執事:將春,敬惟雅況清裕。某山野鄙人,虛名過實,不勝愧負。仲一過京兆,以稠人中,不克款附所懷。繼荷仲晦公特書慰勉,使某寬而居,安而待。其時已為士君子家託二三子相從正句讀,今復十數矣。其束修之供給有餘裕,恩旨益之以奉給,是魚肉而又熊掌也。以義制之,不容再受。且仲可、遵道之生理未治,其事體自是不同。再四辭于宣撫廉公左右,未見從允。靜言思之,將苟避矯激之嫌,必難免士林之誚。託所以解之,非二君子其誰可者?弗獲,即有不安,明公必能見察於言意之外也。區區不已,重附從宜李公,幸矜亮。 恩旨令某充京兆提學。某之寡陋,先生素知,使依先所降恩命教人家子弟,已愧不稱。況提學之職,必習知舉業、場屋有聲者可得為之。而某蹇淺昏昧,一無所曉,何以當此?苟强顏為之,不唯取笑四方,為士友所責,亦恐用非其人,為當路諸公之累。是以傾輸悃愊,冒瀆陳說仲晦、仲一二君子,所願奉致此意,何由使某得守先命,少緩士林之議。便風,不乏伏賜誨藥。邇者從宜李公來,傳道二君子雅意,佩感,但病中不能作書為謝爾。 許衡與劉秉忠、張易二人,大約原來没有什麼交往。第一封信提到“仲一過京兆,以稠人中,不克款附所懷”,當指年張易西行赴聘,在前往六盤山途中路經京兆,因而與許衡有一面之緣。信的開端有“將春”之語,則寫信時間大概已到年年初了。根據《元史》本紀可以知道,忽必烈由大理班師後,在六盤山短暫停留,隨即於年八月回到桓州金蓮川王府。年春,在桓州以東營建開平城,由劉秉忠負責選址和規劃。這段時間,劉秉忠應當就陪侍在忽必烈身邊。而許衡的兩封信告訴我們,、年間,張易與劉秉忠共在一處,也就是說他也同樣陪侍在忽必烈身邊。忽必烈的“潛邸舊侶”人數甚眾,但許多人被派駐中原封地,有的雖然入幕,沒過多久又回歸鄉里。張易的情況則不同,入幕後未見派駐中原或回歸鄉里的記載,大約一直追隨於忽必烈左右。這表明忽必烈對他十分重視。實際上,許衡之所以寫信給劉秉忠、張易,顯然就是由於他們兩人在忽必烈身邊地位特殊,可以代為說項,使自己“得守先命,少緩士林之議”。因此才說:“託所以解之,非二君子其誰可者?”在致信劉秉忠、張易的同時,許衡還給王府中的其他友人另外寫了兩封信,其中一再委託收信人“復言于仲晦、仲一洎諸君子”,“致此意于仲晦、仲一二君子”,請他們“因大用回附片言隻字,以諭撫司,得伸卑懇”。這也表明在許衡看來,張易與劉秉忠一樣是忽必烈幕府的要人,地位高於其他幕僚。有資料顯示後兩封信的收信人是張文謙,這是不無可能的。果真如此,那就意味着,儘管張易入幕比張文謙晚七年,儘管兩人所任同為王府書記之職,但張易在幕府中的實際地位却更高一些。照元人的說法,張文謙當時的角色是“在上(忽必烈)左右主儒者”,而從許衡的信來看,張易似乎更加符合這一角色定位。 對於張易入幕之後的重要地位,前人已經有所揭示。白鋼對許衡的《與仲晦仲一》書信進行了討論,指出:“在許衡眼裏,劉秉忠與張易當時在忽必烈幕府中,處於平起平坐的地位。”但他由此推論張易早在年即已入幕,認為“否則,便不可能成為王府書記,與劉秉忠平起平坐”。這就有問題了。其實,忽必烈對幕僚重用與否,同他們入幕時間早晚並無直接關係。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王文統。王文統是年才被推薦給忽必烈的,推薦人中即包括張易。次年忽必烈即位,首拜文統為中書平章政事,“委以更張庶務”,地位超出張易和其他幕府僚屬。這充分說明入幕時間晚的人,其地位完全有可能後來居上。 那麼,年入幕的張易,在當時為什麼能有後來居上的重要地位呢?大約有兩方面的原因。一方面是劉秉忠的提攜。從現有資料來看,雖然劉秉忠與張易結識可能不算早,但後來却成為莫逆之交。現存劉秉忠《藏春詩集》收錄了寫給張易的詩詞八首。集中作品,投贈對象可考者有限,贈張易者達到八首,已屬最多。諸如“玄鳥欲歸黃鳥斷,詩哦伐木正思君”,“塞下相逢一杯酒,貴傾肝膽略無疑”等句,足見兩人交誼之深厚;而“張翰且休歸故里,謝安應不負蒼生”,“好把中原麟鳳,網來祥瑞皇家”等句,又盡顯劉秉忠對張易之推崇。孟繁清在對相關詩作分析後指出:“詩人和張易有着特殊的親密關係……没有十分深厚的情誼,是寫不出這樣真摯的詩句的。”“也許,在同僚摯友中,真正可以依賴而又有共同語言的只有張易。”兩人的“共同語言”確實很多,因為他們都曾出家為僧,都具有比較駁雜的知識結構和學術取向,以及很強的用世抱負和政治才能。如所周知,劉秉忠在忽必烈身邊具有特殊地位。他既然與張易如此投緣,對張易如此欣賞,自然會大力提攜,提攜到某種程度上與自己“平起平坐”也不算奇怪。另一方面,也與張易本人的個性、能力和才學有關。張易為人“剛明尚氣”,“符士以誠,忤之,不復與合”,早年的坎坷經歷賦予他快意恩仇的江湖習性,這樣的性格更容易得到蒙古統治者的認同。他的政治才能十分突出,有“練達政體”、“臨政善斷”的讚譽,學問方面出入儒、釋、道,兼通天文律曆、陰陽術數,皆非單純的文士可比。因此,其入幕之後能夠脫穎而出,是可以理解的。 然而,由於文獻闕略,我們對張易在幕府中的具體活動所知極少。年的阿藍答兒鉤考事件,似乎並未牽連到張易。這應當是因為張易身居王府,没有直接參與漢地管理工作。年,忽必烈在開平主持佛、道辯論大會。根據《至元辯偽錄》列舉的與會名單,佛教方面包括“少林長老(福裕)”、那摩國師、拔合斯八國師(八思巴)直至“太保聰公(劉秉忠)等三百餘僧”,道教方面包括“張真人(全真掌教張志敬)……等二百餘人”,另有“儒士竇漢卿(竇默)、姚公茂(姚樞)等、丞相蒙速速(孟速思)、廉平章(廉希憲)、丞相没魯花赤、張仲謙(張文謙)等二百餘人”列席會議。其間,並無張易之名。但據同書記載,辯論結束後,有一位道士自稱已有歲,繼續向僧徒挑戰。忽必烈“使僚佐張仲謙、元學士窮考年數”,得知其“乃三十餘歲,本邢州人也”。這裏提到的“元學士”,或許正是張易。因為就目前所知,忽必烈身邊並没有姓元的幕僚,所謂“元學士”,很可能就是“元書記”的另一種表述形式。這樣的話,就說明直到此時,張易與劉秉忠一樣,仍然保持着僧徒身份。在《至元辯偽錄》開列的與會名單中,他大約是被包括在“太保聰公等三百餘僧”或“張仲謙(張文謙)等二百餘人”之中了,故未單列其名。 年,蒙哥汗大舉伐宋,忽必烈奉命單獨統軍南征鄂州。此時張易終於出現在我們的視野裏。王惲《中堂事記》記載: (中統二年六月)八日戊戌,……追諡前經義狀元李俊民為“莊静先生”。(云云)。先生字用章,艧澤人,明昌間進士,道號鶴鳴老人。在河南時,于隱士荊先生傳皇極數學。己未間,聖上在潛,令張仲一就問禎祥,優禮有加。至是先生已歿,其言盡征,故有是命,以旌其德學云。初,張辭去,曰:“繼請以蒲輪來起公。”先生笑不答,贈詩以見方來。……明年正月,先生卒於家。 己未,即年。根據《元史》本紀,這一年二月,南征途中的忽必烈“會諸王于邢州”,當在此短暫停留。李俊民的家鄉是澤州(今山西晉城),距邢州不遠。唐長孺因而推斷“訪問李俊民必在師次邢州時”,其說可從。也就是說,年二月,張易在隨從忽必烈南征經過邢州時,曾奉命到澤州去拜訪李俊民。值得注意的是他被稱為“張仲一”,在當時文獻中首次以俗姓冠于“仲一”之上,很可能表明他已經還俗。聯繫到王惲在張易死後所寫悼詩,其中有句曰“圖回東別鶴鳴軒,脫却山衣相有元”,或許可以大膽推測,張易的還俗就在年二月前後。同年十一月,郝經在向忽必烈所上《班師議》中稱張易為“張仲一”,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。 張易的幕府生涯,可考者大體如上。下一年,忽必烈登上汗位,推行漢法,設立中書省,張易被任命為參知政事,繼而升任右丞,其身份由王府幕僚變成了朝廷宰執。有趣的是,當年在張易出山之際投書求薦的王惲,此時又來到燕京,再次呈上一封《上張右丞書》。與近七年以前的《上元仲一書記書》比較,這封新的上書從內容到用典都頗為雷同。其中回顧了作者與張易上次會面的“往者知遇之故”,更加直白地表達了“出大賢之門,脫囊中之穎,攀逸駕,附驥尾”的迫切心情,明確期望“投書宰相,遂韓愈早達之心,擁帚侯門,要魏勃見知之遇”。由於張易地位的上升,信裏對他吹捧的調門自然也就更高。主要的一段是這樣表述的: 伏惟閣下剛健文明,練達政体,挾漢日則洗光咸池,分蘭省則坐鎮俗雅;忠結主知,學為世用,承恩綸於夜半,洞律管於天心。而復闚其經綸之業,大有高於天下者,不得不為閣下頌之。昔房喬善斷,而如晦矢之以謨;姚崇應變,而宋璟守之以文。四賢者,雖所行不仝,同歸於正,故相須以成,俾無悔事。今閣下極推讓規隨之度,收清寧畫一之功,誠漢室之蕭、曹,聖朝之房、杜也。然念朝廷日遠,天下之事盡在中書,中書之權寔在二三執政。今閣下繋國安危,為世輕重,進退百官,號令天下,所謂仕進之煙霄,一世之龍門也,尚何驥尾青雲之比擬哉?天下之士欲掇青紫、昭名聲者,捨閣下而將安歸乎? 本文的討論,自王惲致張易的書信起始,也就至王惲致張易的書信為止。至於張易入元以後的宦海浮沉,或擬另文探討,這裏就不再贅言了。 (本文在撰寫、修改過程中,南京大學歷史學系劉迎勝、陳得芝教授及翟禹博士、西南民族大學旅游與歷史文化學院講師張衛忠博士,均曾給予有益教示,謹致謝忱。) (本文原载于《文史》年第1期。为方便阅读,删除文中注释。感谢作者授权发布。) : 毛海明,男,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後流動站研究人員; 張帆,男,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。 “观点”栏目主编:黄二宁 本期美编:江雪 毛海明、張帆扫一扫下载订阅号助手,用手机发文章赞赏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shuiwenghuaa.com/swhxw/2827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归入胃经的苦味中药列表
- 下一篇文章: 掌圈泰和泰和大量最新房源,房屋租售